11月16日晚七点,批评理论读书会在知新楼A623进行。批评理论读书会是山东大学文学院较早成立的读书会之一,已经连续进行九个学期。读书会在杨建刚老师带领下穿插阅读中西方文论、当代文论著作,以细读经典,激发同学们的问题意识、培养同学研究兴趣为目的,吸引了本、硕、博三个学生群体参加,在阅读与分享中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每学期读书会都会将与会同学的发言、感悟编辑装订成册,作为读书会成果留存。
本学期批评理论读书会选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文学图像论》两本著作进行阅读。本学期计划以四次读书会时间研读重点书目《文学图像论》,并以本次《文学图像论》读书沙龙来揭开研读《文学图像论》的序幕。同时,读书会有幸邀请到该书的作者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赵宪章教授莅临指导。本次沙龙由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杨建刚教授主持,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韩清玉教授、陈硕老师以及文学院众多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读书沙龙。
读书沙龙开始之前,杨建刚教授对赵宪章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他的研究历程,重点介绍了他近年来的研究领域:文学图像论和文学书像论。

读书沙龙开始,2021级硕士杨晨雪同学发表读书感悟。她讲到,赵宪章教授的《文学图像论》内容很丰富,吸收了大量哲学、语言学、图像学、美学等资源,而且产生了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术语,创造了具有理论阐释效力的概念范畴,对语言与图像的关系研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很有理论深度。通过阅读赵老师的文章以及《文学图像论》,对“文学书像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赵宪章教授提到书像是作为汉字形体的“艺术扮相”,将书像纳入文学图像论,并且书中提到早在西汉萧何就有“书者、意也”的说法,东汉蔡邕续补到“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我们称魏晋南北朝为文的自觉时期,是否也可以找到一个古代的书像自觉时期。今天的文学与图像则表现为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的矛盾——图像符号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僭越本属于语言的领地。图像对文字进行了一种侵蚀,这种趋势会越演越烈还是会逐渐偃旗息鼓,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2022级硕士谭吉瑞谈到,《文学图像论》中提到玛格丽特的《形象的背叛》,书中阐述到其中的图像和文字互相矛盾,文字对图像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但是对于一个不懂法文的人来说,这个所谓的“文字”是无法给他传达意义的,也就是说文字可以忽视,图像在他眼里就是“一只烟斗”。扩展来说,很多语图文本对于不识字的读者来说是不存在语言和图像之间复杂关系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赵老师所做的研究是一种内部研究,不考虑观者的接受?《文学图像论》中谈到图像只能表现有的,不能表现无的事物,从这里可以想到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在古文字的发源之初,文字和图像是含混的,所以中国古代就有“书画同源”的美学命题,书法也由此成为中国艺术中最具有代表性和特色的艺术。宗白华先生就强调书法艺术的重要性,毕加索也声称自己如果更早接触和学习中国书法,那他将会是一位书法家,而不是画家。
2021级硕士丁雪媛谈到,对赵宪章老师《文学图像论》中讲到的语言和图像作为符号的意义很感兴趣。赵老师在书中指出语言和图像作为符号时,属性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有两点。第一个是结构的不同,第二个是指向的不同。杨建刚教授之前提到过,语言的优点就是叙述持续性的动作,图像的优点是描绘同时并列的物体。语言的时间性是绵延的,词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自身,而是更多地存在于它自身之外的地方,一旦我们把握了它的内涵或识别出某种属于它的外延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词了。这表明语言符号从能指到所指的路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顺序。而图像作为一种瞬间的定格的符号、一种隐喻符号,其意义就在于它本身,我们需要在反复的观看和凝视它,才能理解它的意义。语言和图像在结构上的不同,导致他们二者具有不同的指向。维特根斯坦就说:“你要是看到了,有些话你就不会说了。”这实际上就是揭示了人类的语言能力有可能在图像观看中趋向萎缩的可能——对于视觉图像的沉迷会让我们罹难失语症之患。这也是当下学界认为图像会取代语言的一种担忧。
2022级硕士刘怡笑认为赵宪章教授的《文学图像论》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书中的理论启发我们去关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去思考图像时代文学与图像如何共存,如何更好地借助图像获得文学的新生。刘怡笑巧妙地关注到了《文学图像论》的封面:上端是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下端是墨绿色的纯色底,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的书法贯穿上下两部分。赵老师在书中曾提到了古代小说中的插图,由此思考,在图像时代,实体书籍的封面是否能算作一种“新插图”?书籍封面和书籍的内容又能否算作一种“语图互文”?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的印刷的质量不断提高,封面的精美多样是其最直观的表现。同时,在网络文学以及电子书籍的冲击下,实体书籍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生存危机。为了吸引消费者,增加销量,出版商们在封面设计上煞费苦心。当然,书籍的封面本身就是书籍的一部分,可以说其决定了读者对书籍的第一印象,有情怀、负责任的出版社及作者,也会在书籍的封面上下功夫。刘怡笑将现在市面上较常见、较具代表性的书籍封面分为了四类:第一类是为了消费而生的所谓网红小说;第二类是当代作家的作品,以余华的《活着》为例;第三类是经典的学术理论著作,以《小逻辑》为例,最后一类是实用性的教辅书籍,从四类代表性的书籍封面进行观点论述。
2021级硕士王彦丁认为,赵宪章教授是从现实中的案例追溯到文学艺术的根基上去做文学图像学的研究,具有很深的学术积淀,又到了一个大道至简的境界,令我们高山仰止。身处于一个“图像时代”,我们始终能够听到一种担忧的声音,即认为从“读文字”到“读图”是人类的退步。确实,从历史的视野与当下的生活来看,我们都能感到文字与图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层级关系。文字更具有抽象性,更理性,有一定精英色彩;而图像是感性直观的,更能带来情绪冲击,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换一种角度来看,“图像时代”的到来未必是一件坏事。图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因为它比文字更能渗入那些不被精英关注的“下层市场”。图像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方式,显然门槛更低、更有大众色彩,在技术的支持下,它使过去与文化绝缘的人也成为了文化的享有者。图像的大获全胜看似是一种退步,却亦是文化前所未有地普及的一种进步的表现。
2022级博士生刘强注意到了图像对文字的反抗潜能。他提出,生活在“大他者”笼罩的时代,图像能够表达文学所不能表达出的韵味,并且在语言形成之前,图像可能已经存在。那为什么后来语言渐渐代替了图像,或者是图像不再成为一种主要的表达符号,也是因为人们交流需要语言,语言文字更能承担起作为交流工具的角色,追求一种表达效率。因此,在当今的读图时代,在某种层面上,图像对文字的僭越,是一种感性的启发,比如一些“无题”的画,画的意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我们要回到最原初的语境中,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2019级博士生鲜林提到,早在汉代,王充就意识到了当时人们过分关注图像,导致轻视文字的趋势。而赵老师的《文学图像论》站在当前这样一个读图时代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文学和图像的关系问题,和两千年前的王充形成了一种回响。赵老师在论文和《文学图像论》中也谈到了关于人物画和故事画的问题,老师认为人物画和故事画的区别在于单纯的人物画是表现个人,和周围的东西不发生联系,而故事画中,两个人物形象之间会产生关系,所以变成了展现两个人或者是多个人物之间的这种故事的场景。但是鲜林注意到其实我们在很多图像之中会发现,可能画中只是表现单个人,但是它的某种姿态是展现他在某个故事场景中的某种形象,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描绘典型事件中所呈现的形象,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单纯的人物画,但是其实也是在展现人物在某个故事中的一个场景,所以人物画和故事画之间的区别还值得继续讨论。

韩清玉教授针对同学的发言进行回应。他讲到,提起“书像自觉”概念,我们可以注意到宗白华提出的一个观点:“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这一点是研究书法、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学者大多忽略的,我们甚至可以以书法为核心确定艺术史的分期,以及从书法中凝练中国美学范畴。韩清玉教授提出,我们不要站在文学本位来观看图像艺术,比如电影。当我们在阅读安妮宝贝(庆山)的小说《七月与安生》的时候,会发现相对于改编的电影来说,小说的语言表达是单一、苍白的,但是改编的电影可以表现出文字所难以表达的意味,这涉及到图像叙事和文学语言叙事之间的关系问题。韩老师回忆在美国访学时看到的画展中有很多“无题”的画作,并提到阿瑟·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关于“无题”的观点:“无题”至少暗示了这是一件艺术作品;以“无题”命名本身也是留给观众自己去解读的空间;当然即使是“无题”,也是画家自己拟定的,作为创作的最后一项程序,本身暗示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同时,韩清玉教授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古诗中的“无题”与西方绘画中的“无题”是不同的。

陈硕老师回应同学们提出的“书画是否同源”这一命题。他认为画家多赞成这一说法,书法家的论述不多。我们看到的有关书画同源的文献,在清代以前基本上都是画家讲的,因为画家要攀附书法家来提高自身声望。关于象形字是不是等于图像这个问题有待商榷,甲骨文按照六书来分,形声字比例较高,反映的一个直接问题是甲骨文不是脱离于语言存在的,所以一旦和语言捆绑到一起,它就已经变成一个语言化的注解了。在《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中也谈到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表意符号的存在,不代表书画一定同源,因为那个年代也会有自己的官方图像。同时,陈硕老师提醒同学们不要迷信图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古画名字都是后来人配的,还有很多题画诗中,文本和图像是完全脱节的,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因此,我们必须辩证看待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不要迷信权威,否则容易掉入“以图证史”的陷阱。
杨建刚教授认为赵宪章教授提出的“文学图像论”是当代文论非常重要的领域,《文学图像论》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从文学的细处着眼,在往往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发掘理论问题。研读赵老师的著作要学会去发现问题,关注赵老师中西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中西对话,文明互鉴。赵老师的研究引领了当今文论研究的方向。我们研读《文学图像论》的过程是进入文学图像研究的过程,也是聚焦当今文论研究热点的过程。现在的研究大多是理论内部的自我生产,而赵老师直面文学现象,通过对现象的阐释提炼理论问题。比如在《文学图像论》的61页中赵老师所列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图像和文章叙述出现错位的问题,这会导致一种阐释的悖论,同时导致文字对图像真实性的解构。杨建刚教授认为从赵老师的逻辑论证可以得出,图像是一种虚指符号,语言是一种实指符号,这个话题是很值得探讨的。小说的电影改编是从语言媒介到图像媒介的转变,而这种改编要适应图像媒介的呈现方式。杨建刚教授提醒大家,虽然我们经常讲有图有真相,但是图像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其实图像也是一种可以处理的虚拟的故事,比如鲍德里亚所讲的拟真与仿真。杨建刚教授谈到对文学图像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继续阅读赵老师的《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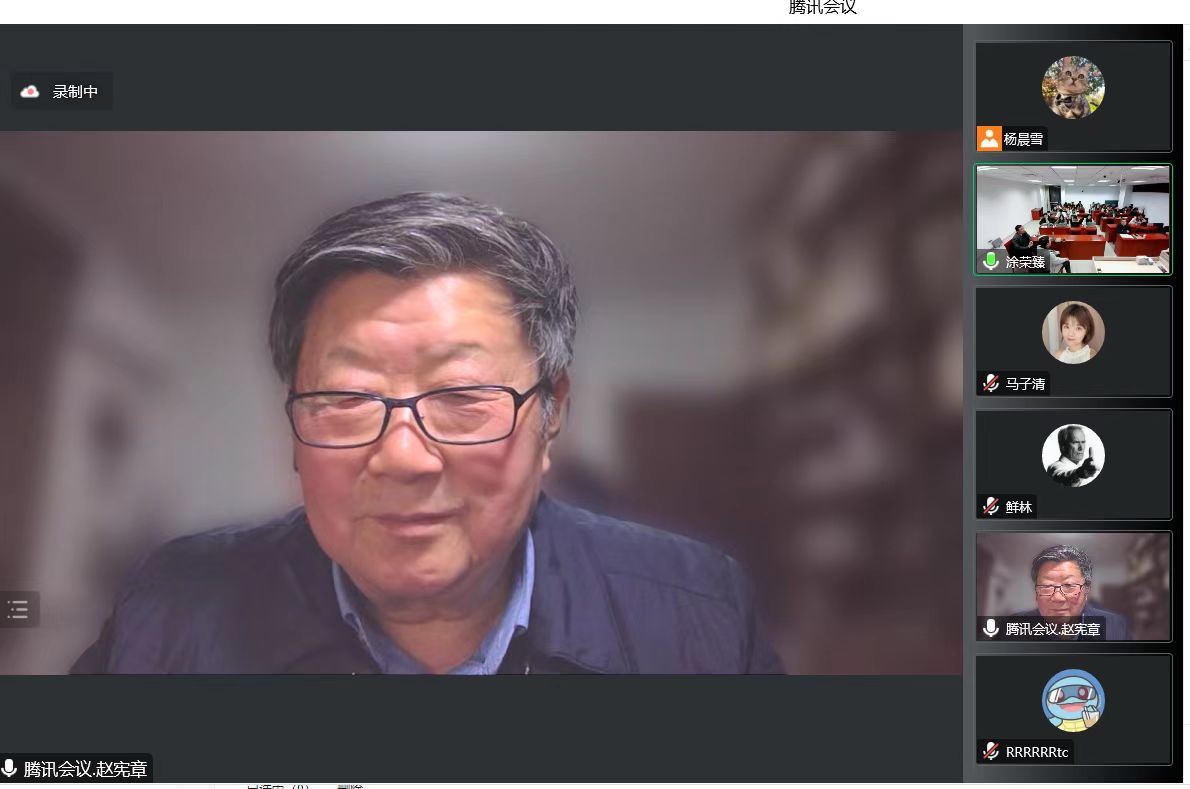
最后,赵宪章教授指出,读书会这种形式是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获得知识、增长思考、发现问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赵宪章教授从同学们对于《文学图像论》这本书的热议,感受到山大浓厚的学术氛围。接着,赵宪章教授针对老师和同学们的讨论进行补充。首先,赵宪章教授提出,中国的美学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自上而下,而中国的美学是自下而上的建构,从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出发总结概括出来具有经验性的理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肯定宗白华先生所说以书法为核心,并且从书法中凝练中国美学范畴,也就是以文艺现象为中心,去重审中国的美学史。中国的美学建构应当注重文学艺术的经验,这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第二,在影视艺术没有出现之前,文学和图像这两种符号是一种长期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图像符号的表意功能受技术的支持,赋予图像艺术越多的技术,图像的表意功能越强大,这种强大就意味着对人的吸引力、诱惑力越来越强大。当下社会中图像传媒是最强势的传媒,表现出对语言符号的僭越和替代。第三,赵宪章教授认为书法艺术能够把这两种符号有机地联合在一起,书法艺术既是语言符号又是图像符号,语言和图像的矛盾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解决,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问题,因此书像论成为赵宪章教授最近着力较多的领域。

杨建刚教授对赵宪章教授莅临读书会表示再次感谢,并且提出文学图像论、文学书像论将会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同时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今后以批评理论读书会为契机,畅所欲言,收获新识。至此,《文学图像论》读书沙龙圆满结束。
赵宪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历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推崇“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学术理念。目前从事文学图像和文学书像研究。出版《文学图像论》《文艺学方法通论》《西方形式美学》《文体与形式》《文学变体与形式》《文体与图像》等,主编10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出版)和学术辑刊《文学与图像》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
(文/杨晨雪 图/黄长明)
